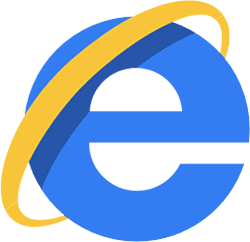前言
在城乡规划与土地管理行政执法实践中,违法建设的查处是维护规划秩序、保障公共利益的重要环节。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违法建设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城市治理中的难点。然而,当违法建设行为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死亡时,行政机关往往面临程序推进、责任认定、文书送达等诸多法律难题。此类案件的处理既关系到公共利益的维护,也涉及继承人及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情形的处理也存在诸多争议。本文旨在通过系统分析相关典型案例,结合现行法律法规,探讨违法建设行为人死亡后拆违案件推进中的法律问题,以期为行政执法实务提供参考。
违法建设作为一种持续性的违法行为,其违法状态不因行为人的死亡而自动消除。根据《行政强制法》第二条、第四十四条的规定,行政强制措施针对的应是“违法行为所造成的非法状态”,而行政强制拆除的规制对象是“违法建筑”而非“违法建设行为人”。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对关于违反规划许可、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建设、设计违法行为追诉时效有关问题的意见》(法工办发〔2012〕20号)的指示,违反规划许可的行为因其带来的违反城乡规划的事实持续存在,应当认定其行为具有继续状态。因此,只要违法建筑仍然存在,其对规划秩序的破坏就持续存在,行政机关仍有权继续推进查处程序,直至违法状态消除。
在司法实践中,亦有相关案例支持上述观点。例如,在(2018)苏0791行初541号案件中,违法建设者已死亡,违法建筑仍存在且被他人用于经营,对此法院明确指出:强制拆除决定指向的拆除对象是违法建筑物,违法建筑物的建设者死亡不影响行政机关对该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在(2019)浙1102行初93号与(2020)浙11行终123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违法建设行为造成的违法状态具有持续性,而行政处罚追诉时效应当自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现今,责令限期拆除、强制拆除决定、强制拆除行为一般应认定为行政强制措施与政强制执行行为),案涉房屋虽于1996年完工,但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的行为一直处于持续状态,被告对此进行处罚符合规定。
违法建设行为人的继承人/违法建筑的实际管理使用人是否为拆除义务主体?
(一)司法实践中的分歧与统一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对此大致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继承人/实际管理使用人可列为行政程序当事人。例如,在(2019)浙1102行初93号案件中,原告徐某1通过继承成为案涉违法建筑(第五层及屋顶)的实际占有人,并长期使用该房屋,法院认为,被告丽水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其认定为行政处罚的当事人并无不当之处。
第二种观点认为,违法建筑不能作为合法财产予以继承,不应将继承人/实际管理使用人认定为“义务主体”。例如,在(2020)苏06行终4号案件中,二审法院明确指出:实际管理使用人并不必然是拆除义务主体,违法建筑不能作为合法财产予以继承;限期拆除是法律规定的违法建设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原则,既然上诉人陆冠林及两原审第三人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人或受益人,更不是违法行为人,即使作为原行为人的子女实际占有该房屋,也不负有限期拆除该房屋的法律责任。
(二)笔者观点
1、继承人:因违法建筑非合法遗产,不承担拆除义务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可见,违法建筑因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违反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非法建筑”,不符合“合法财产”的构成要件,无法作为遗产被继承人继承。基于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继承人未继承违法建筑的“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自然无需承接“拆除义务”。但若继承人实际占有、使用违法建筑,作为违法建筑的实际管理使用人,行政机关虽不能要求其承担拆除义务,但可要求其履行配合执法、清理物品、腾退房屋等协助义务。
2、实际管理使用人:属于配合义务主体,亦非拆除义务主体
除前文所述继承人因实际占有、使用违法建筑成为违法建筑的实际管理使用人的情形之外,违法建筑承租人、受让人、借用人等亦属于实际管理使用人。实际管理使用人虽未实施违法建设行为,但因实际控制违法建筑,与“违法状态的消除”存在直接关联——若其拒不腾退,行政机关无法顺利实施拆除,违法状态将持续存在。因此,实际使用人虽非“拆除义务主体”,但属于“配合义务主体”,行政机关可将其列为行政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保障其陈述、申辩权,并要求其履行配合义务。
(一)文书制作:准确列示相对人,规范叙述违法事实
1、文书标题和称谓
行政相对人需具备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已死亡行为人丧失民事权利能力和行政行为能力,无法成为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若行政机关仍将其列为相对人,将导致文书主体不适格,面临被撤销的风险。例如,在(2022)黑71行终77号案件中,水务交通局在已知违法建设行为人管某祥于2011年死亡和其妻子邓某红为案涉建筑实际使用、管理人的情况下,于2021年先后作出《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限期拆除违法建筑物构筑物决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均以管某祥为 “行政相对人”,法院认为,行政机关明知行为人死亡,仍以其为相对人作出文书,导致行政命令和行政决定缺乏执行主体,属于认定事实不清、主体错误,最终判决撤销《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
因此,行政机关不宜继续使用已死亡行为人的姓名作为当事人,建议采用“某某违法建设相关利害关系人”等概括性称谓。
2、事实认定部分
行政机关可在文书中提及已死亡行为人,以完整叙述违法事实。例如,在(2018)苏0791行初541号案件中,法院认为,强制拆除决定书中关于“违法行为人:庞兰英(已亡)”及其生前有关自然情况的记载和表述,无论从其表述本身,还是从整个决定书的行文、内容准确理解之,这种行文表述只不过是为完整、全面叙事而己,毫无将已亡的庞兰英确定为所谓主体的意思。
因此,笔者虽不建议行政机关将已死亡行为人列为相对人,但为清晰说明违法建筑的来源(谁建设、何时建设),可在文书中提及已死亡行为人,明确其违法建设行为人的身份,但需注明其已死亡的情况,以避免歧义。
3、权利义务告知
文书除了要求继承人、实际管理使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清理财物、腾退房屋外,还应详细告知告知其享有的申辩、陈述等权利。
(二)文书送达: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保障知情权
1、优先直接送达,规范处理“拒签”情形
在(2022)黑71行终77号案件中,水务交通局向已死亡的管某祥留置送达《行政强制执行决定书》,送达回证未注明“留置原因”“送达人姓名”,且未附现场照片。二审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明知管某祥死亡的情况下,仍向其留置送达,且送达回证不规范,属于送达程序违法。在(2018)苏0791行初541号案件中,东海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向庞兰英送达《限期拆除决定书》时,庞兰英拒签,送达回证注明“直接送达,当事人拒签”,并附现场照片。原告朱某1主张 “拒签即未送达”,法院认为,留置送达是直接送达的一种方式,送达回证备注清晰,有照片佐证,应认定文书已送达。
因此,对已知的继承人、实际使用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应优先采取直接送达方式。若当事人拒绝签收,可依法采取留置送达,但需在送达回证上注明拒签原因、送达人姓名、见证人情况,并拍照、录像留存证据(如记录送达过程),避免因送达回证无备注被认定为未送达。
2、慎用公告送达
公告送达属于“最后送达方式”,仅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时方可适用。若行政机关已知利害关系人的联系方式(如电话、住址),不得直接采用公告送达,需先尝试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等方式。若不确定是否还有其他利害关系人,行政机关可在向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尝试送达的同时,在违法建筑所在小区的公告栏或者违法建筑物外墙张贴相关文书。
(一)听证程序的适用问题
强制拆除不属于行政处罚,不适用《行政处罚法》中的听证程序。但是,行政机关应当保障利害关系人的陈述、申辩权利。
(二)追诉时效的计算问题
违法建设行为具有继续状态,追诉时效应从行为终了之日起算(法工办发〔2012〕20号意见)。违法行为人死亡不影响追诉时效的计算,因为违法状态仍在持续。行政机关应当注意收集和保存证据,证明违法状态的持续性。
(三)避免程序空转的问题
行政机关应及时履职,避免无正当理由超期办理。违法行为人死亡不是拖延案件处理的正当理由。行政机关应当建立相关工作机制,确保案件及时推进。
结语
违法建设行为人死亡并不导致案件必然终结,行政机关仍应依法推进查处程序,但需注意对象认定、文书送达、程序正当性等关键环节。在执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应当坚持依法行政原则,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既要维护行政管理秩序,又要保障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唯有如此,才能实现维护城乡规划秩序与保障个体合法权益的双重目标,提升行政执法的合法性与公信力。